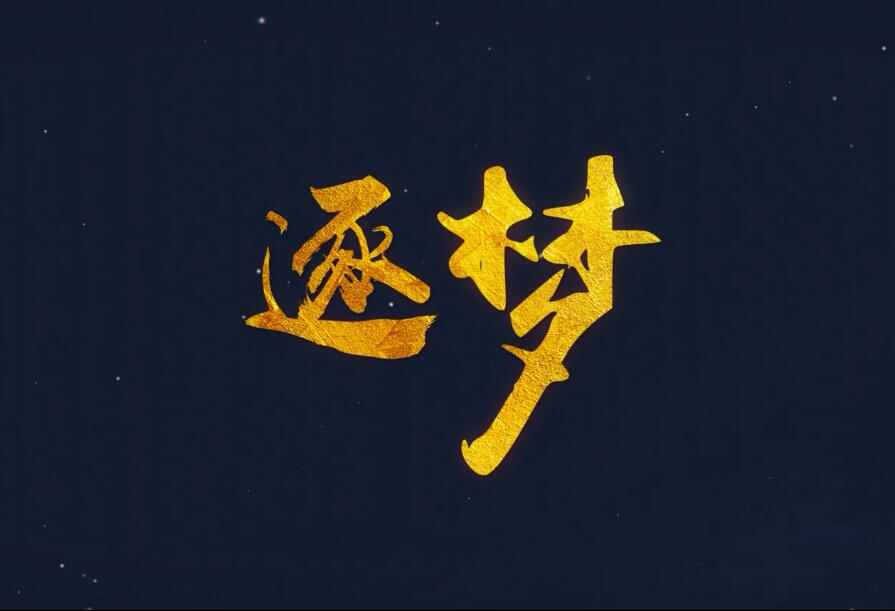记忆中的时光:小麦熟了
发布时间:2025-07-01 17:09:52 作者:黄伟东 来源:朔黄运输分处 访问量:651车轮碾过乡间土路时,卷起细碎的麦秸与黄土。我望着窗外翻滚的金浪,麦穗低垂的弧度里藏着夏日的重量,仿佛又回到小时候耳畔突然响起父亲的呼喊:“快起来了,小懒虫!今儿要开镰了。”记忆像被阳光晒暖的麦粒,噼里啪啦的绽开细密的裂缝。
那时的村里会在麦收前夜陷入奇异的寂静。家家户户将磨得锃亮的镰刀挂在屋檐下,月光淌过刀刃时泛着银亮的水纹。父亲总会在凌晨四点时把我摇醒,竹筐里的烙饼还冒着热气,铁耙与扁担碰撞出清脆的声响。田间小路上渐渐浮动着密集的身影,露水打湿的裤脚在晨雾中若隐若现。麻雀似是炸了窝般腾空而起,惊醒了整个麦季。
镰刀破开麦秆的脆响此起彼伏,父亲教我左手攥住麦秆根部轻轻扶倒,右手刀锋斜斜掠过。断茎处渗出青涩的汁液,沾在指缝里像抹了层琥珀色的糖浆。我总在捡拾遗漏的麦穗时,被麦芒扎得龇牙咧嘴,却又忍不住钻进刚捆好的麦垛里打滚。新割的麦秸经过太阳炙烤后会散发出阵阵清香,混着汗水的味道在空气里发酵成独特的乡愁。
正午的蝉鸣最盛时,远处传来柴油机的轰鸣。打麦场上的脱粒机喷吐着金黄的麦粒,扬起麦糠织成的金色帷幕。男人们光着膀子搬运麦袋,汗水顺着脊背淌进裤腰;女人们端着绿豆汤穿梭其间,笑声惊飞了偷食的麻雀。我踮脚趴在麻袋堆顶,看着麦粒如瀑布倾泻进麻袋时,突然被父亲一把抱起抛向半空,麦糠雪花般落在我们身上。
暮色四合时,整片田野只剩下整齐的麦茬泛着金黄色。归途中父亲肩头的麻袋压出深深的沟壑,我却抱着我那拾来的半袋麦穗蹦跳着不肯撒手。炊烟升起的地方,母亲正用刚脱壳的麦粒煮粥,乳白的雾气漫过窗棂,裹着麦香渗进每个毛孔。
如今柏油路早已取代了土路,联合收割机几分钟便能吞掉整片麦田。但每当看见泛黄的麦浪,总会想起那个在麦垛间捉迷藏的午后,想起父亲教我捆麦时粗糙的掌心,想起母亲用新麦熬的粥里浮着油星。那些被麦芒扎过的手背,被麦秸染黄的衣襟,最终都化作血脉里流淌的乡音,在每个麦熟时节悄然苏醒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