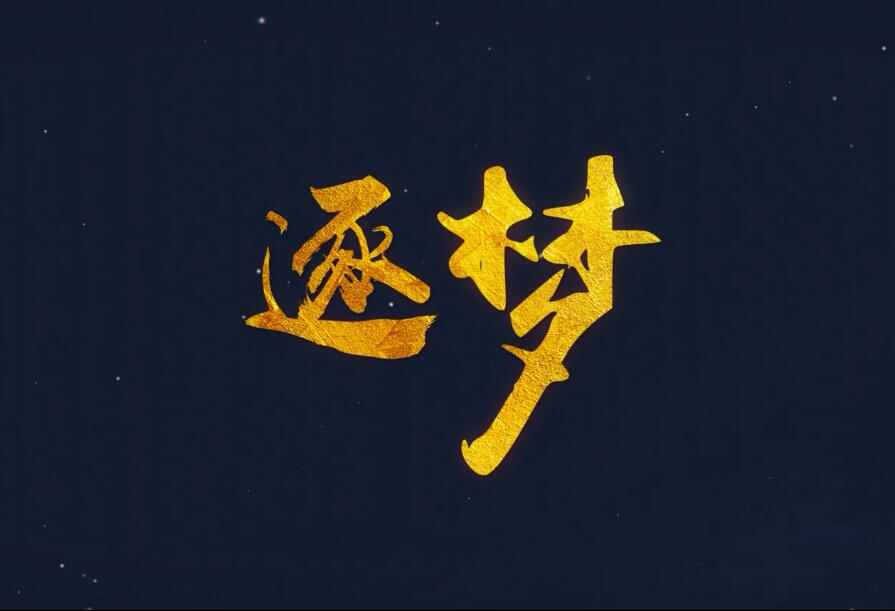门外与窗前
发布时间:2017-01-10 10:55:41 作者:管理员 来源:管理员 访问量:527关上门,就关上了半个世界。门外,有太多的颜色,有太多种声音。那里还有刺眼的阳光,张牙舞爪地向人扑来。关上门,会有另一束阳光映进来,映在窗前。
我喜欢坐在窗前向外看,透明的玻璃隔去了喧嚣,收纳了风景。但在我的窗前,有那么一群人,似乎总无法与风景相适宜。
他们穿着蒙了一层灰的衣服,戴着黄色的安全帽,拖着双很旧的鞋,提着空了的塑料水杯。他们说着让我听不懂的方言,大声地笑着在小区里走着。他们是给我的邻居装修的民工。
我坐在窗前,悄悄地把目光落在他们身上。
午休时的民工们,或坐或躺在邻居的屋檐下。他们会围在一起吃盒饭,互相借火抽烟,又大笑着说着我听不懂的方言。他们总用愉快的语调聊天,时不时咧开嘴笑一笑。他们卸去了半日的劳累,我从中看到了甚至是我也不曾拥有的简单的快乐。他们在聊些什么?是在说晚上摆一桌酒菜慰劳慰劳自己?还是在说远在老家还在穿开裆裤的孩子?
我坐在窗前看着,他们发现不了我的目光,更发现不了我的目光渐变疑惑。他们忍受着雇主无礼的呵责,行人无言的轻视,和那钢筋水泥凭着自己高楼林立的虚荣投来的冷傲的目光。但却为何,他们总会愉快地笑?
那天,看他们的水都已喝完,我便给他们递了壶水。不再从窗前,我推开门,看着门外的他们。接我水的是个小伙子,和他身后的工友一样满脸惊讶。他用手来接,而当他手快碰到水壶时,他却突兀地停下了。水壶是干净的淡色,而他的手褐黄又布满灰,茧和伤口混在一起,还有刚擦过汗的颜色。眼看那只手又要收回,我连忙将水壶塞给他。他僵硬地道谢,却高兴地回去和工友分水。他们笑着喝水,笑着和我说蹩脚的普通话,笑着彼此奇怪的发音。和他们对了话后才发现,他们会那么轻易地选择相信,他们有烦恼却努力制造快乐。他们的世界,有着热烈的温度。
在门外,让我认识了他们。他们艰难地生活在门外的世界,却坚持守护自己的快乐。他们在门外用自己勤劳的双手的劳作,努力使自己跟上时代的脚步,努力维护着自己的一小片天地,也偶尔轻轻地幻想着门内的人投来几道友善的目光。但或许,他们本并不是格格不入的,只是追求的风景,没有包含他们罢了。而去包含,也是很简单的事。
到门外,投出几道友善的目光,说出一句问候,递上一条毛巾……他们就会用自己的信任接受似乎微不足道的关怀。
推开门,推开半个世界。门外,有真正的温暖。(汪洋)